

发布时间:2022-03-07源自:本站作者:admin阅读(344)
“精神病学”技术自18世纪起,精神卫生中心在对精神障碍的治疗中,通过药物与机械约束来控制和恢复神经系统是极常用的方法。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大西洋两岸一直流行着一种相当粗陋但有效的精神药理学。但精神病院的隔离环境为更多掌控疯癫的“精神病学”技术带来可能性,这些技术将能够直接控制人的思想、激情和意志。这些方法特别吸引批评者们,他们批评机械束缚(用镣铐、锁链束缚疯人)是残忍且适得其反的,会激惹病人原本想要缓解的狂暴。从18世纪50年代起,在启蒙运动的名义下,人们开始提精神卫生中心倡新的治疗方法,强调“道德”(现代术语为“心理”)方法——仁慈、理性、人道。道德治疗的支持者认为,精神失常与天花这类生理疾病不同,它是一种精神障碍,是糟糕的教育、不良习惯及个人苦难(如失去亲人的创伤、破产,或是恐惧地狱之类的宗教惊恐)的产物。它需要不同的精神疗法。正如前文已经提示的那样,这些新的心理学方法具有更深层的基础。从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剧作家们将激情戏剧化,展示了内心折磨——欲望与责任、愧疚与悲伤——如何造成人格分裂。在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突出了意精神卫生中心识对塑造身份的作用。笛卡尔思想的英国继承者、伟大的批评者约翰·洛克将疯癫描述为逻辑过程失常或想象力失控的产物(这一观点后来为塞缪尔·约翰逊所强调)。1690年,洛克写道,“自然状态中的缺陷”,似乎是由心智缺少灵敏、活力和运动缺乏所致,因而被剥夺了理性;而疯子似乎受到另一个极端的影响。因为在我看来,疯子没有丧失推理能力;但常常把某些想法错误地结合在一起,误以为是真理;他们将从错误的原则中推出的结论视为正确的。因为想象发生扭曲,他们将幻想当作现实,将错误当成正确。精神卫生中心而启蒙运动时期的反叛者让-雅克·卢梭的著述则预示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1930)的诞生。卢梭提出,现代文明的压力使人与灵魂疏离,产生分裂的自我。 因此,理解精神错乱的心理学方式的基石出现了。提倡这种认识模式的人,认为通过精神病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密切的人际互动,可以克服精神错乱,精神病院就是进行这种活动的合适场所,因为这是完全由医生来调控的环境。所谓的“道德管理者”有效地通过个人魅力,依靠性格的力量和创造性的心理战术,智胜失常者的反常行为。首先,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必须制服患者,然后通过操纵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希望、恐惧,他们对自尊的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关键是,通过影响疯子仍能唤醒和训练的残余的正常情绪,以恢复其休眠的人性。1790年前后,意大利的温琴佐·基亚鲁吉、巴黎的菲利普·皮内尔、约克疗养院的图克家族以及德国的约翰·雷尔及其他浪漫主精神卫生中心义精神病学家的解放性思想将这种构想向前推进了几个阶段。根据“道德治疗”原则,这些改革者重视仁慈、冷静和理性,旨在将患者视为能够重生的人。皮内尔在精神病学领域发起的“精神卫生中心法国大革命”将疯子从文字和形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恢复他们作为理性公民的权利。借鉴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这些改革者强调,疯子与白痴不同,他们并未完全丧失推理的能力。约克疗养院的图克家族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由智力过程(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软件”)的错误而引起的妄想。疯子深陷于幻想世界中,那是无拘无束的空想的产物。他们需要像任性的孩子一样被对待,需要严格的精神规训,以及思想和情感的再训练。因此,精神病院应该成为一所教养院。1800年前后,这样的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学在高尚乐观主义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精神病院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治疗。整个19世纪开展了大规模的运用道德疗法治疗疯人的计划,毕竟,如果这种开明的精神病院能使精神病患者恢复正常,将他们安置在这种机构不正是社会的责任吗?在整个欧洲及北美,国家在立法及照顾疯人方面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出现了管理疯子的、新的精神病学职业。精神病院变成了疯子的家。尽管改革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大多数时候,精神病院经常被证明是一座监狱。19世纪的疯癫博物馆19世精神卫生中心纪的丰功伟绩之一是它成为精神病学发展的先驱时代。1852年,查尔斯·狄更斯回忆道,在不那么久远的过去,对外在身体的强迫,对内在进行狂热的物理治疗是……针对精神失常者的特定疗方。锁链,稻草,肮脏的孤独状态,黑暗和饥饿;每年春秋两季,无论状况好坏,每个病人都要给服大量的药喇叭、沙棘糖浆、酒石化锑及吐根;接受在旋转仪器上旋转、体罚、堵嘴、“持续醉酒”等治疗,没有什么太过疯狂过分的药方,没有什么太过畸形残酷的药方是疯子医生开不出来的。一切都变了!狄更斯宣称,残忍的行为精神卫生中心受到了遏止,善良是我们的座右铭,贝德莱姆精神病院这些传统的收容所(令人回忆起从前那些糟糕的治疗手段和悲惨的日子)都被调查和改造。私立精神病院受到了严格的管理。18世纪的精神病院曾是个秘密的空间,避开了公众的监督。19世纪的改革者们使之完全置于社会的监视之下。像约翰·米特福德《霍思顿及贝思纳格林的沃伯顿私人精神病院内部的罪恶与恐怖》这样的事实揭露,推动着人们迫切想要纠正那些不当的虐待性治疗。对疯子的收容管理已从权宜之计转变为一种具有治精神卫生中心疗目标和理想的制度。例如,在法国,菲利普·皮内尔的改革及《拿破仑法典》的规定在1838年划时代的《精神卫生法》中得以体系化了。该法要求,每一个省或建立自己的公立精神病院,或要保证为疯子提供适当的设施。为了防止非法监禁,该法确立了对精神失常者进行认证的规则(不过,对于贫穷的精神失常者,只要有行政官员的签字即可)。地方行政长官有审查权。比利时在1850年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在英国,许多既得利益的医疗团体害怕私立疯人院的利益会受到威胁,因而强烈反对改革,但政府还是精神卫生中心颁布了类似的改革方案。揭露一系列关于非法监禁理智健全之人(这是重罪)的丑闻导致了一项重要的立法保障。1774年颁布的《疯人院法案》规定了基本的许可和认证。根据该法规定,所有的私立疯人院都必须持有地方法官颁布的许可证。许可证每年的续期取决于入院登记册的维护是否令人满意。地方法官有权进行视察(在伦敦,视察机构是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最重要的是,除了贫民外,所有人都需有医疗证明(苏格兰对疯人院及其公共管理有另一种不同的制度)。在疯人院丑闻导致英国精神卫生中心议会委员会于1807年和1815年对疯人院进行调查之后,英国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伯利恒疯人院因严重管理不善被取缔(此前不久去世的外科医生布赖恩·克劳瑟也曾精神错乱到需要穿紧身衣的地步)。19世纪20年代起,一系列法律的通过加强了1774年法案。最初在伦敦市(1828),后来在全国(1844)确立了精神疾病鉴定人制度。精神疾病鉴定专员由固定的检查人(包括医生、律师和政府官员)组成,负责报告精神病院的运作情况。他们有权起诉,以及吊销许可证。他们还负责规范、改善护理和治疗条件。他们坚持要求对病人精神卫生中心进行适当记录,并记录所有的人身胁迫案件,以尽量杜绝最严重的虐待行为。防止不当监禁的保障措施被进一步加强。根据1890年的一项合并法案,包括贫民在内的所有患者,都必须有两份医疗证明。从长远来看,这种防止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院被滥用为监狱机构的法律条文主义关切可能已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这种观念过于强调只有那些被正式确诊为精神失常者的人才能进入精神病院,因而延迟了精神病院向更为灵活的“开放式”机构转化的进程,所谓“开放式”机构是指患者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入院或出院。反之,精神病院被当作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因而确诊也就意味着长时间的关押。这样一来,精神病院便无法为那些暂时性精神错乱患者、不完全的精神失常患者以及轻度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适当的机构式照护。在欧洲和美国,19世纪见证了精神病院和精神病患者数量的惊人增长。在英格兰,1800年仅有几千名患者,而到1900年,患者人数已达10万左右(全国总人口增长速度不到此的一半)。美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1850年住院患者不到5000人,到1904年则超过15万人。到1950年,英国共有15万名精神病患者被送进专门机构,精神卫生中心而美国更多达50万人。在一些新的民族国家,患者人数也飞速上升。以意大利为例,1881年共有1.8万名受到监禁的患者,在以后的35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这种数量上的增长并不难解释。官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心态使得人们对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对实实在在的机构充满信心。管教所、监狱、医院、精神病院——据称,所有这些机构都将解决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从来不乏对精神病院的批评声音。从早年开始,“贝斯莱姆”便成为人类虐待同类的代名词。患者的精神卫生中心抗议越来越多,抱怨受到粗暴对待和疏忽大意的照料,如1796年发表的戏剧化的《对人类的讲话,附一封写给托马斯·芒罗医生的信:一份制造精神失常者并没收其财产的收据;以及一张真正微笑的鬣狗的素描》,作者——曾经的患者威廉·贝尔彻。医学界的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总是怀疑将精神病患者聚集在一起的功效。尽管如此,支持者的人数远远多于怀疑者,精神病院运动在乐观主义的浪潮中得到了鼓舞。这种情况注定会改变。19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一种新的悲观主义逐渐蔓延。统计数据显示,期望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院成为灵丹妙药是没有根据的。治愈率似有下降,而在公立的精神病院里,长期住院的患者越来越多。精神科医生成了他们自己观点的受害者。他们曾警告称,人类社会充满了迄今为止仍未知的精神疾病——只有他们可以治愈这些疾病。他们提出了诸如“偏执狂”“偷窃癖”“嗜酒狂”“道德失常”等类别,并坚持认为许多传统上被定义为恶习、罪恶和犯罪的反常行为实际上都是精神失常,应该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们还鼓励地方法官将那些屡教不改的罪犯从济贫院或监狱转出。但精神病院精神卫生中心的负责人则发现,要实现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问题比预料到的更多。此外,老年人和痴呆者,以及癫痫患者、瘫痪患者、三期梅毒患者、共济失调患者,还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都日益被大量收进精神病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患者的预后十分悲观。精神病院成了患者在彻底失去治愈希望时的最后选择。慢性患者人数增多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疯癫也许比想象中更具威胁。精神病院刚建成不久,就挤满了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酗酒者、习惯性手淫者、性癫狂者、神经病患者、麻痹性痴呆患者和其他精神卫生中心神经功能缺陷患者。更糟的是,痛苦的经验证明精神疾病并未如预期中那样得到康复。精神病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从治疗康复的地方变成了“废品收集站”。批评者称,精神病院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正是它造成了制度化的疾病。对精神病院的信心本身会否是一种错觉?精神病院的拥护者则反驳说,问题的根源不在精神病院,而在患者自身。假如精神病学全力以赴仍不能产生疗效,岂不是说明许多形式的精神失常确实是不治之症?这种观点鼓励了新的生物医学理论的发展,1900年时,精神卫生中心这些理论将精神病描述为一种遗传性污点、一种脑部的污点。对那些整天面对精神病院中的活死人,或是研究各种精神障碍的神经病理学的几代精神科医师来说,清醒的现实主义指向了“退化论”:精神失常与生俱来,会随着世代相传日趋严重。这一结论很契合社会政治精英对于大众社会和大众民主所致威胁的忧虑情绪。退化和精神分裂症为了分析和分类精神疾病,人们付出了卓绝的努力。精神病院的兴起、精神病专家的崛起以及神经病学的进步,都激发了这种巨大的努力。精神卫生中心这一专业需要通过破解社会心理疾病的秘密向社会证成自己。因此,它承担了将精神病病理化的任务。精神病学不断宣称要“发现”先前不曾被怀疑的精神疾病。过度饮酒被医学化为“酗酒”,鸡奸等性虐待被精神病化为“同性恋神经症”,德国精神病医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1886年出版了开创性的《性精神病态》,精神病理学捕获了许多其他色情“变态”现象:人兽性交、粪性淫乐、露阴癖、恋物癖、鞭打、虐待狂和受虐狂、异装癖等。有这些异常行为的孩子、妇女、同性恋者和其他一些性变态者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精神卫生中心往往遭到监禁。退化主义精神病学也从文学天才和艺术家,如印象派和立体派颓废的气息中看出了精神疾病。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这些人的感觉系统一定处在病态失调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一些人越来越担心乌合之众的危险的退化。许多精神病学家警告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只有适应社会的人才能生存时,这些人正以精神愚痴危害着文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在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中达到高潮:让疯子可以摆脱枷锁,恢复理智。然而,一个世纪以后,精神病学却变得更加悲观。精神卫生中心德国精神科医师埃米尔·克雷佩林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早发性痴呆”一词,不久后瑞士医生厄根·布洛伊勒将其命名为“精神分裂症”。如克雷佩林在1901年的《临床精神病学讲稿》中所说,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呆傻,相反,他可能聪明和精明到令人震惊。然而,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性,放弃了接触人类社会的期望,退缩到封闭的自我世界中。克雷佩林用“情感萎缩”和“意志损害”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的主张,即这些患者是道德变态,与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差不多是相同类别。退化主义精神病学还有更加可怕的假想——令人发指的种族主义、遗传主义和性迷恋——这些都遭到了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于20世纪初兴起的心理动力学的拥趸的强烈批驳。在精神分析的中心发生了治疗学的创新,提出另一项乐观的新方法:谈话治疗。现代心理医学20世纪以来,人们努力了解精神疾病,建立其分类学,并调查其发病原因。特别重要的是,对精神疾病(严重的精神错乱,包括逃避与现实接触的自闭行为)和神经官能症(病情相对较轻)进行了重大区分。这一划分被普遍认为是区别器质性病因和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性病因的基础。而在精神疾病患者中,又进一步区分了躁狂抑郁症(双相障碍)与精神分裂症。尽管如此,关于精神疾病的描述和分类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议。浏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编写的专业诊断手册《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就可发现关于精神疾病的定性一直在变化。该手册每隔几年就要大力修订一次,其本身就是饱受争议的对象。它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甚至常常相互矛盾或重叠的术语的增长,有些术语这一版被删除,下一版又出现。1975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举办了一次臭名昭著的邮寄精神卫生中心投票的民意调查,导致同性恋被延迟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删除。有很多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政治文化、种族以及性别歧视仍影响着对所谓客观疾病的诊断。部分由于人们对胰岛素治疗和电休克治疗等暴力疗法的敌视,1950年后出现的精神药物广受欢迎。精神药理学多年来一直充斥着无用的药物,如溴化物和巴豆油(一种使患者失去行动能力的强力清洗剂)。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神药物(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氯丙嗪、用于治疗躁郁症的锂制剂)在稳定患者行为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精神卫生中心这使得患者可以离开精神病院那种受庇护却无温情的环境。患者自己对大量用药(精神安定剂)的反应比较模糊,因为药物能引起嗜眠及精神呆滞(“僵尸”效应)。吉米·莱恩先前是一名患者,他描述了“氯丙嗪踢腿现象”:“你会看到一群人坐在一间屋子里,所有的人都会不自主地向上踢腿。”药物革命仍未完成。大约一代人之前,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廉·萨金特及该行业其他领军人物曾预言,氯丙嗪之类的特效药将在1990年使精神疾病完全消失。这一愿望至今仍未实现。回到原点?正如我们看到的,精神精神卫生中心病院运动造成了自己的危机,病人并未如期康复。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发展精神病院的计划仍处在初级阶段时,就连精神病学家也承认巨大的精神病院无异于巨大的恶魔。现代反精神病学运动诞生前的整整一个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已看到了制度化的不良影响,许多精神疾病被认为是由精神病院这种号称能治愈它们的机构引起的。在对精神病院最尖锐的批评中,有一些就来自精神病院的患者。常见的控诉有两种:一种是在家人的授意下对精神正常的人进行非法或不适精神卫生中心当的强制监禁,其隐秘目的是推翻遗嘱或抛弃丑妻;另一种是对肉体的残暴行为。因此,长期以来,精神病院都遭受着合法性危机,但鲜有作为。药物革命、为患者争取权利的运动、精神病院濒临崩溃的严峻问题(财政部的吝啬对此推波助澜),这些结合在一起,在英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为流行的“非监禁化”政策。1980—1989年间,英国关闭了30家精神病院,且政府批准到1995年再关闭38家。这一最新的重大突破有其讽刺之处,人们对此十分熟悉。一方面,药物革命只成功了一半。更糟的是,虽然推行了“社区护理”,精神卫生中心却鲜有资金投入,对社区也没有给予认真考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度公开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首相本人处于妄想状态的一个症状)。妄想状态迄今仍然存在。部分原因是这种怪兽的本质仍不为人所知。托马斯·萨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写道:“精神病学的传统定义是一种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医学专业。我认为,这个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将精神病学放在了炼金术和占星学的行列中,使其成为伪科学的一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精神疾病’这样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一观点带来了思想解放,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太无情了,而大多数人认为是在夸大其词。然而,事实是,即使是萨斯的批评者们,在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因此,理解精神错乱的心理学方式的基石出现了。提倡这种认识模式的人,认为通过精神病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密切的人际互动,可以克服精神错乱,精神病院就是进行这种活动的合适场所,因为这是完全由医生来调控的环境。所谓的“道德管理者”有效地通过个人魅力,依靠性格的力量和创造性的心理战术,智胜失常者的反常行为。首先,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必须制服患者,然后通过操纵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希望、恐惧,他们对自尊的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关键是,通过影响疯子仍能唤醒和训练的残余的正常情绪,以恢复其休眠的人性。1790年前后,意大利的温琴佐·基亚鲁吉、巴黎的菲利普·皮内尔、约克疗养院的图克家族以及德国的约翰·雷尔及其他浪漫主精神卫生中心义精神病学家的解放性思想将这种构想向前推进了几个阶段。根据“道德治疗”原则,这些改革者重视仁慈、冷静和理性,旨在将患者视为能够重生的人。皮内尔在精神病学领域发起的“精神卫生中心法国大革命”将疯子从文字和形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恢复他们作为理性公民的权利。借鉴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这些改革者强调,疯子与白痴不同,他们并未完全丧失推理的能力。约克疗养院的图克家族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由智力过程(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软件”)的错误而引起的妄想。疯子深陷于幻想世界中,那是无拘无束的空想的产物。他们需要像任性的孩子一样被对待,需要严格的精神规训,以及思想和情感的再训练。因此,精神病院应该成为一所教养院。1800年前后,这样的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学在高尚乐观主义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精神病院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治疗。整个19世纪开展了大规模的运用道德疗法治疗疯人的计划,毕竟,如果这种开明的精神病院能使精神病患者恢复正常,将他们安置在这种机构不正是社会的责任吗?在整个欧洲及北美,国家在立法及照顾疯人方面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出现了管理疯子的、新的精神病学职业。精神病院变成了疯子的家。尽管改革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大多数时候,精神病院经常被证明是一座监狱。19世纪的疯癫博物馆19世精神卫生中心纪的丰功伟绩之一是它成为精神病学发展的先驱时代。1852年,查尔斯·狄更斯回忆道,在不那么久远的过去,对外在身体的强迫,对内在进行狂热的物理治疗是……针对精神失常者的特定疗方。锁链,稻草,肮脏的孤独状态,黑暗和饥饿;每年春秋两季,无论状况好坏,每个病人都要给服大量的药喇叭、沙棘糖浆、酒石化锑及吐根;接受在旋转仪器上旋转、体罚、堵嘴、“持续醉酒”等治疗,没有什么太过疯狂过分的药方,没有什么太过畸形残酷的药方是疯子医生开不出来的。一切都变了!狄更斯宣称,残忍的行为精神卫生中心受到了遏止,善良是我们的座右铭,贝德莱姆精神病院这些传统的收容所(令人回忆起从前那些糟糕的治疗手段和悲惨的日子)都被调查和改造。私立精神病院受到了严格的管理。18世纪的精神病院曾是个秘密的空间,避开了公众的监督。19世纪的改革者们使之完全置于社会的监视之下。像约翰·米特福德《霍思顿及贝思纳格林的沃伯顿私人精神病院内部的罪恶与恐怖》这样的事实揭露,推动着人们迫切想要纠正那些不当的虐待性治疗。对疯子的收容管理已从权宜之计转变为一种具有治精神卫生中心疗目标和理想的制度。例如,在法国,菲利普·皮内尔的改革及《拿破仑法典》的规定在1838年划时代的《精神卫生法》中得以体系化了。该法要求,每一个省或建立自己的公立精神病院,或要保证为疯子提供适当的设施。为了防止非法监禁,该法确立了对精神失常者进行认证的规则(不过,对于贫穷的精神失常者,只要有行政官员的签字即可)。地方行政长官有审查权。比利时在1850年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在英国,许多既得利益的医疗团体害怕私立疯人院的利益会受到威胁,因而强烈反对改革,但政府还是精神卫生中心颁布了类似的改革方案。揭露一系列关于非法监禁理智健全之人(这是重罪)的丑闻导致了一项重要的立法保障。1774年颁布的《疯人院法案》规定了基本的许可和认证。根据该法规定,所有的私立疯人院都必须持有地方法官颁布的许可证。许可证每年的续期取决于入院登记册的维护是否令人满意。地方法官有权进行视察(在伦敦,视察机构是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最重要的是,除了贫民外,所有人都需有医疗证明(苏格兰对疯人院及其公共管理有另一种不同的制度)。在疯人院丑闻导致英国精神卫生中心议会委员会于1807年和1815年对疯人院进行调查之后,英国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伯利恒疯人院因严重管理不善被取缔(此前不久去世的外科医生布赖恩·克劳瑟也曾精神错乱到需要穿紧身衣的地步)。19世纪20年代起,一系列法律的通过加强了1774年法案。最初在伦敦市(1828),后来在全国(1844)确立了精神疾病鉴定人制度。精神疾病鉴定专员由固定的检查人(包括医生、律师和政府官员)组成,负责报告精神病院的运作情况。他们有权起诉,以及吊销许可证。他们还负责规范、改善护理和治疗条件。他们坚持要求对病人精神卫生中心进行适当记录,并记录所有的人身胁迫案件,以尽量杜绝最严重的虐待行为。防止不当监禁的保障措施被进一步加强。根据1890年的一项合并法案,包括贫民在内的所有患者,都必须有两份医疗证明。从长远来看,这种防止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院被滥用为监狱机构的法律条文主义关切可能已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这种观念过于强调只有那些被正式确诊为精神失常者的人才能进入精神病院,因而延迟了精神病院向更为灵活的“开放式”机构转化的进程,所谓“开放式”机构是指患者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入院或出院。反之,精神病院被当作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因而确诊也就意味着长时间的关押。这样一来,精神病院便无法为那些暂时性精神错乱患者、不完全的精神失常患者以及轻度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适当的机构式照护。在欧洲和美国,19世纪见证了精神病院和精神病患者数量的惊人增长。在英格兰,1800年仅有几千名患者,而到1900年,患者人数已达10万左右(全国总人口增长速度不到此的一半)。美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1850年住院患者不到5000人,到1904年则超过15万人。到1950年,英国共有15万名精神病患者被送进专门机构,精神卫生中心而美国更多达50万人。在一些新的民族国家,患者人数也飞速上升。以意大利为例,1881年共有1.8万名受到监禁的患者,在以后的35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这种数量上的增长并不难解释。官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心态使得人们对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对实实在在的机构充满信心。管教所、监狱、医院、精神病院——据称,所有这些机构都将解决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从来不乏对精神病院的批评声音。从早年开始,“贝斯莱姆”便成为人类虐待同类的代名词。患者的精神卫生中心抗议越来越多,抱怨受到粗暴对待和疏忽大意的照料,如1796年发表的戏剧化的《对人类的讲话,附一封写给托马斯·芒罗医生的信:一份制造精神失常者并没收其财产的收据;以及一张真正微笑的鬣狗的素描》,作者——曾经的患者威廉·贝尔彻。医学界的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总是怀疑将精神病患者聚集在一起的功效。尽管如此,支持者的人数远远多于怀疑者,精神病院运动在乐观主义的浪潮中得到了鼓舞。这种情况注定会改变。19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一种新的悲观主义逐渐蔓延。统计数据显示,期望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院成为灵丹妙药是没有根据的。治愈率似有下降,而在公立的精神病院里,长期住院的患者越来越多。精神科医生成了他们自己观点的受害者。他们曾警告称,人类社会充满了迄今为止仍未知的精神疾病——只有他们可以治愈这些疾病。他们提出了诸如“偏执狂”“偷窃癖”“嗜酒狂”“道德失常”等类别,并坚持认为许多传统上被定义为恶习、罪恶和犯罪的反常行为实际上都是精神失常,应该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们还鼓励地方法官将那些屡教不改的罪犯从济贫院或监狱转出。但精神病院精神卫生中心的负责人则发现,要实现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问题比预料到的更多。此外,老年人和痴呆者,以及癫痫患者、瘫痪患者、三期梅毒患者、共济失调患者,还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都日益被大量收进精神病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患者的预后十分悲观。精神病院成了患者在彻底失去治愈希望时的最后选择。慢性患者人数增多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疯癫也许比想象中更具威胁。精神病院刚建成不久,就挤满了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酗酒者、习惯性手淫者、性癫狂者、神经病患者、麻痹性痴呆患者和其他精神卫生中心神经功能缺陷患者。更糟的是,痛苦的经验证明精神疾病并未如预期中那样得到康复。精神病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从治疗康复的地方变成了“废品收集站”。批评者称,精神病院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正是它造成了制度化的疾病。对精神病院的信心本身会否是一种错觉?精神病院的拥护者则反驳说,问题的根源不在精神病院,而在患者自身。假如精神病学全力以赴仍不能产生疗效,岂不是说明许多形式的精神失常确实是不治之症?这种观点鼓励了新的生物医学理论的发展,1900年时,精神卫生中心这些理论将精神病描述为一种遗传性污点、一种脑部的污点。对那些整天面对精神病院中的活死人,或是研究各种精神障碍的神经病理学的几代精神科医师来说,清醒的现实主义指向了“退化论”:精神失常与生俱来,会随着世代相传日趋严重。这一结论很契合社会政治精英对于大众社会和大众民主所致威胁的忧虑情绪。退化和精神分裂症为了分析和分类精神疾病,人们付出了卓绝的努力。精神病院的兴起、精神病专家的崛起以及神经病学的进步,都激发了这种巨大的努力。精神卫生中心这一专业需要通过破解社会心理疾病的秘密向社会证成自己。因此,它承担了将精神病病理化的任务。精神病学不断宣称要“发现”先前不曾被怀疑的精神疾病。过度饮酒被医学化为“酗酒”,鸡奸等性虐待被精神病化为“同性恋神经症”,德国精神病医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1886年出版了开创性的《性精神病态》,精神病理学捕获了许多其他色情“变态”现象:人兽性交、粪性淫乐、露阴癖、恋物癖、鞭打、虐待狂和受虐狂、异装癖等。有这些异常行为的孩子、妇女、同性恋者和其他一些性变态者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精神卫生中心往往遭到监禁。退化主义精神病学也从文学天才和艺术家,如印象派和立体派颓废的气息中看出了精神疾病。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这些人的感觉系统一定处在病态失调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一些人越来越担心乌合之众的危险的退化。许多精神病学家警告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只有适应社会的人才能生存时,这些人正以精神愚痴危害着文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在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中达到高潮:让疯子可以摆脱枷锁,恢复理智。然而,一个世纪以后,精神病学却变得更加悲观。精神卫生中心德国精神科医师埃米尔·克雷佩林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早发性痴呆”一词,不久后瑞士医生厄根·布洛伊勒将其命名为“精神分裂症”。如克雷佩林在1901年的《临床精神病学讲稿》中所说,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呆傻,相反,他可能聪明和精明到令人震惊。然而,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性,放弃了接触人类社会的期望,退缩到封闭的自我世界中。克雷佩林用“情感萎缩”和“意志损害”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的主张,即这些患者是道德变态,与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差不多是相同类别。退化主义精神病学还有更加可怕的假想——令人发指的种族主义、遗传主义和性迷恋——这些都遭到了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于20世纪初兴起的心理动力学的拥趸的强烈批驳。在精神分析的中心发生了治疗学的创新,提出另一项乐观的新方法:谈话治疗。现代心理医学20世纪以来,人们努力了解精神疾病,建立其分类学,并调查其发病原因。特别重要的是,对精神疾病(严重的精神错乱,包括逃避与现实接触的自闭行为)和神经官能症(病情相对较轻)进行了重大区分。这一划分被普遍认为是区别器质性病因和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性病因的基础。而在精神疾病患者中,又进一步区分了躁狂抑郁症(双相障碍)与精神分裂症。尽管如此,关于精神疾病的描述和分类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议。浏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编写的专业诊断手册《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就可发现关于精神疾病的定性一直在变化。该手册每隔几年就要大力修订一次,其本身就是饱受争议的对象。它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甚至常常相互矛盾或重叠的术语的增长,有些术语这一版被删除,下一版又出现。1975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举办了一次臭名昭著的邮寄精神卫生中心投票的民意调查,导致同性恋被延迟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删除。有很多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政治文化、种族以及性别歧视仍影响着对所谓客观疾病的诊断。部分由于人们对胰岛素治疗和电休克治疗等暴力疗法的敌视,1950年后出现的精神药物广受欢迎。精神药理学多年来一直充斥着无用的药物,如溴化物和巴豆油(一种使患者失去行动能力的强力清洗剂)。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神药物(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氯丙嗪、用于治疗躁郁症的锂制剂)在稳定患者行为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精神卫生中心这使得患者可以离开精神病院那种受庇护却无温情的环境。患者自己对大量用药(精神安定剂)的反应比较模糊,因为药物能引起嗜眠及精神呆滞(“僵尸”效应)。吉米·莱恩先前是一名患者,他描述了“氯丙嗪踢腿现象”:“你会看到一群人坐在一间屋子里,所有的人都会不自主地向上踢腿。”药物革命仍未完成。大约一代人之前,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廉·萨金特及该行业其他领军人物曾预言,氯丙嗪之类的特效药将在1990年使精神疾病完全消失。这一愿望至今仍未实现。回到原点?正如我们看到的,精神精神卫生中心病院运动造成了自己的危机,病人并未如期康复。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发展精神病院的计划仍处在初级阶段时,就连精神病学家也承认巨大的精神病院无异于巨大的恶魔。现代反精神病学运动诞生前的整整一个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已看到了制度化的不良影响,许多精神疾病被认为是由精神病院这种号称能治愈它们的机构引起的。在对精神病院最尖锐的批评中,有一些就来自精神病院的患者。常见的控诉有两种:一种是在家人的授意下对精神正常的人进行非法或不适精神卫生中心当的强制监禁,其隐秘目的是推翻遗嘱或抛弃丑妻;另一种是对肉体的残暴行为。因此,长期以来,精神病院都遭受着合法性危机,但鲜有作为。药物革命、为患者争取权利的运动、精神病院濒临崩溃的严峻问题(财政部的吝啬对此推波助澜),这些结合在一起,在英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为流行的“非监禁化”政策。1980—1989年间,英国关闭了30家精神病院,且政府批准到1995年再关闭38家。这一最新的重大突破有其讽刺之处,人们对此十分熟悉。一方面,药物革命只成功了一半。更糟的是,虽然推行了“社区护理”,精神卫生中心却鲜有资金投入,对社区也没有给予认真考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度公开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首相本人处于妄想状态的一个症状)。妄想状态迄今仍然存在。部分原因是这种怪兽的本质仍不为人所知。托马斯·萨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写道:“精神病学的传统定义是一种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医学专业。我认为,这个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将精神病学放在了炼金术和占星学的行列中,使其成为伪科学的一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精神疾病’这样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一观点带来了思想解放,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太无情了,而大多数人认为是在夸大其词。然而,事实是,即使是萨斯的批评者们,在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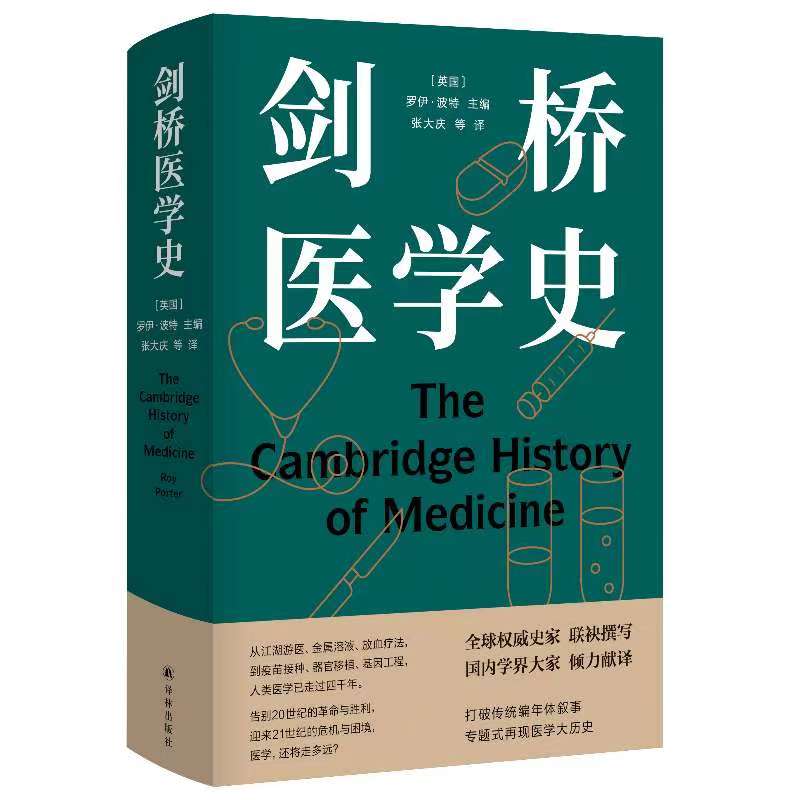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英]罗伊·波特主编、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欢迎分享转载→ http://qq023.com/jingshen/818.html